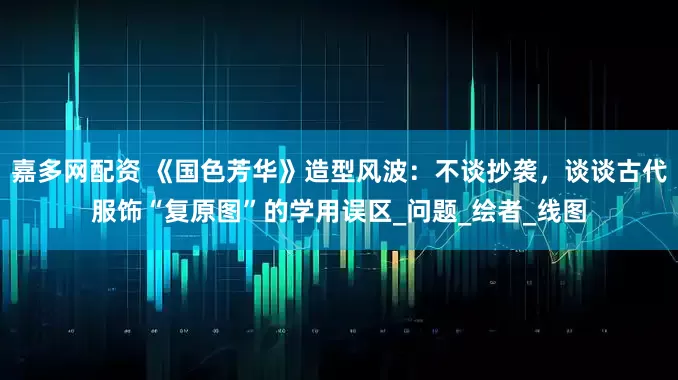
本文作者: 春梅狐狸
新书《图解传统服饰搭配》已上线,请多支持
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开这一篇。虽然我不针对某个人,但应该会得罪好多人。但这个问题又是普遍存在的,的确产生了许多误解与歧义,在我看来是很值得讨论一下的,所以还是把这篇写完了(又是刻意冷放了三个月才发)。
应该很多人之前也吃到了这个瓜,就是《中国妆束》的作者在网上说古装剧《国色芳华》未经授权直接照搬了书中的造型,属于商用。
具体截图如下——
展开剩余95%(作者原帖截图、配图,图/小红书)
因为《国色芳华》这个剧我也没看,也没打算去看,所以到底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界定,我就不做判定了。至于后续剧方和作者和解之类,我也没细看是怎么个情况(毕竟我跟古装剧向来只有被捂嘴删文的经历,这已经超出我认知范畴了),只是想聊聊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背后的一些认知观察——
很多绘画类的古代服饰、传统服饰书,尽量就当作绘本看,而不是复原。
我本来以为这算是一个大家对于这类书籍应该具备的比较基础的认知,但这个瓜吸引我关注的、事件让我吃惊的是,真的有很多人是把这类书“直接当教科书看的”。
(讨论帖评论区截图,图/小红书)
然而仔细想想,我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毕竟曾经谁没把下面这套图当成圭臬过呢,现在应该还出现在各种书籍论文、博物馆展板里吧。
(网络图片)
甚至于我都觉得自己当年犯的错更理直气壮,毕竟这套图的画法比起现在的风格,是不是看起来更像“教科书”些,莫名还有种五十步笑百步的骄傲感。这套图是先流出这些图片,后来大家才看到书。虽然在这套图流传的时候,已经有人质疑部分图片了,但看到书以后质疑的声音就更多了,问题集中在这几方面——
①史料可信度问题,比如用清朝资料画明朝的示意图;
②绘制还原度问题,比如文物上是往左,示意图上画成了向右;
③模糊点呈现问题,比如一些图文资料有所欠缺或争议的但又必须要绘制出来的部分,要怎么呈现。
对于如今的相关书籍,我另外补充两条——
④参考对象的翔实度问题,明明有更贴切的绘制参考对象,但给出的却是一些周边资料作为依据;
⑤绘图还原度的一致性问题,同一本书中既可能存在近似临摹的图,也可能存在创想设计的图,而区分又很模糊,而读者往往容易有信赖惯性。
在读者端呢,也有一些问题存在,尽管我们不爱总结自己的问题——
①图像资料的依赖性,这类书拿到手基本只看图,对文字内容看得很粗浅;
②缺乏看图的思辩性,基本是画啥信啥,不看绘图的考证过程,尤其一些画手很容易脑补却存疑的细节部分,却又是读者最深信不疑的;
③读图的理解差异,这个和上面的②差不多,图像本身的传达能力也是因人而异。
读者以外的群体,或者说并非单纯读者身份的群体,也可以再补充一条——
④利益驱使下的言论遮掩,就是明明知道绘图存疑,但为了一些商业利益、流量导向而睁眼说瞎话。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事件里窥见端倪。
比如第一处被作者指出电视剧的“照搬”,相关讨论帖中的评论区已经有网友给出了作者和书中都没有放的、更贴切的绘制参考对象,文物线图其实和《中国妆束》书中绘制的效果是很接近的。
(作者原帖配图,图/小红书)
(讨论帖评论区截图,图/小红书)
上面那位网友的附图中,右侧的线图出自《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一书。我另外补充同为章怀太子墓的另外几幅石刻线图,大家可以自己先试着理解一下这些都应该是什么样的
(《中国妆束》书中插图与文物线图对比)
(章怀太子石刻线图,图/《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
头上的凤鸟饰物,我个人推测可参考现藏于纳尔逊博物馆的唐代金凤或风格类似的其他文物(可以对照一下翅膀以及顶部的花簇图案)。凤鸟立体对称,且初始状态应该镶有绿松石等珠宝,藏品状态下脱落或腐朽了。
(《中国妆束》书中插图与文物照对比)
(还残留部分镶嵌的唐代金凤)
很显然,书中给出的绘图可以有另外更贴切的参考对象,翔实度需要存疑,细节模糊点的呈现与原件有明显差异,并且按照作者的发言,绘制效果在还原作者意图上也有所缺失。
后面那点还可以补充几句,一般来说这类书籍最好的情况是作者就是绘者(有些书不一定给绘者署名,也容易造成误解),或者绘者本身也参与考证,否则在交流上产生问题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抛开这些不说,《国色芳华》显然也不是犯了一个很有创意的错误,至少十年前我就见过了。
比如,由于很多人对于古画的透视不太理解,将正面立体的鸟冠做斜向扁平的情况很常见。至于将画师笔下应该是立体的鸟,做成平面浮雕效果,就是类似于《国色芳华》里的这种做法,都快成传统手艺了。我2014年在微博就喷过这个问题,而且还是抄画的指责别人抄袭自己,属于笑话闭环了(我都想申请自己拥有指责这个错误的原创版权了)。
(微博截图及配图)
而这个鸟是立体的还是平面的,是正摆的还是侧放的,顶着官方合作的学者复原里也常常是混乱不堪,同样的团队在不同的秀场里会出现不同的答案。
(莫高窟130窟壁画形象复原,一会儿正放一会儿斜摆)
(莫高窟130窟壁画临摹,左为段文杰,右为常沙娜)
而另一处作者指出的“照搬”……可能要算两处,但这个妆面的问题我是真没看懂(我个人觉得是不同绘者的画风影响更大些吧),可能是我不会化妆的原因吧,留给大家讨论。
(作者原帖配图,图/小红书)
(《国色芳华》同造型剧照局部,图/豆瓣)
只说这个花钿吧。作者只在小红书笔记里提到了参考对象是“晚唐壁画”,没提具体信息,应该是莫高窟第9窟供养人像的史苇湘临摹版,定语这么长是因为原壁画已经看不出有花钿了。
(莫高窟9窟壁画,图/《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莫高窟9窟史苇湘临摹画)
原书并有文字特别提及这个花钿的来源,是直接出现在“隋唐五代女子典型妆容一览”章节下的“金靥”“花靥”形象里(我直接放书里的图不会因此而被炸掉整篇文章吧)。我也去豆瓣找了《国色芳华》 更多剧照,将史苇湘临摹版、《中国妆束》插图以及剧照都摆在这里了,大家可以自行判定是否属于“照搬连笔触都没变”。
(莫高窟9窟史苇湘临摹画局部,图/@身在北海北)
(《中国妆束》书中插图)
(《国色芳华》剧照局部,图/豆瓣)
这个例子可以正好说一下读者端的一些问题,这里形成了好几对有趣的关系。吃瓜人是作者小红书笔记拼图的读者,《国色芳华》剧组是《中国妆束》的读者,而书的作者应该也是史苇湘临摹画的读者。每一个读者角色,是不是对被读的对象有足够的思辩,是不是能从图像中获得相同的理解呢?
仅以我个人为例,我会觉得史苇湘临摹画是有透视变形和艺术笔触的。我理解的花钿是装饰意味比较浓的,图形应该是匀称规整的,而不是偏向涂鸦写意风格。若建立在史苇湘对临摹画作的个人加工不多的基础之上,我会猜测原型是五瓣花形。你也可以不同意,这是我们对史苇湘临摹画理解的差异,除了每个人的观察与联想不同,见过的花钿种类和熟悉程度也会导致差异化的判断。
(左为莫高窟61窟欧阳琳临摹画局部,右为莫高窟98窟范文藻临摹画局部)
(各式花钿,图《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比如最近看到的另一个所谓古画“现实版”,很明显“现实版”找错了原画里发髻部分平面与立体的关系。尽管通过模特姿势、服装颜色等模仿,与古画拼贴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很相似,实际却是从发型到服饰都不相符(这种所谓“复原”现在网上遍地都是)。
但也没有做成什么特别奇怪的东西,而是做成了清宫剧里“剪秋姑姑”的那种发型。很显然,比起古画里的样子,这个仿版更熟悉清宫剧里的那些发型。
(清宫剧中的“剪秋姑姑”发型)
(“剪秋姑姑”发型可能的历史原型)
(冷枚 《春闺倦读图》中的发型参考)
这也是我们之前屡次提到过,人无法超越自己的认知,当他需要具象化一个事物但又不清楚这个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自己认知中觉得相似或相关的东西拿出来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影视剧里的造型考据很别扭的原因,因为剧组的人见过的影视造型远多于他们看过的文史资料,细节十分容易走样,且依然走回影视的老路。
这个瓜里最好判定的其实是《国色芳华》有没有参考《中国妆束》这本书?一定是看了,而且剧组大概率看的参考资料也不会很多,尤其是偏向于壁画原貌、文物原照、研究论文等这类没有被“加工”成可直接参照的形象资料剧组应该是看得很少,不足以支撑剧组在细节处填上这本书以外吸收到的认知(真看了我上面那些内容就该是剧组或者粉丝搬出来了,而不是等这剧都播完了、凉透了我这个没看过剧的人冒着得罪人的风险来一一列出)。
比较难以判定的是这种参考算不算一种抄袭(虽然作原帖的用词是“照搬”)?这个难点不在于《国色芳华》剧照与《中国妆束》插图的相似程度有多高,而在于《中国妆束》插图在文物资料基础上的再创作成分有多少,是否拥有创作的独特性和专属性。
然而,这又会陷入另一个困境。因为在一般理解中,历史题材的绘画必然是作者的个人独创成分越少、内容就越贴近历史原貌(其实这需要具体分析),这个书也就越好卖,在推广宣传上也会向这个方向引导。
(书籍在电商平台的宣传主图)
从相关讨论帖的评论区也可以看出,的确很多人是分不清这类书籍的“二创”,这里不仅包括是否了解复原绘画是否存在“二创”,还包括如何分辨绘画中哪些部分是属于“二创”的。毕竟,如果有些部分是从文物转绘而来,不存在二次设计,即便有一些商用使用了“照搬”方式也很难界定为侵权(此处使用的是公众标准,亚文化圈或粉圈那种创意类似就算抄袭的逻辑不在此列)。
(讨论帖评论区截图,图/小红书)
就像本文开头说得,绘画类的古代服饰、传统服饰书本来就不应该被当作百分百复原来看待,甚至于多年前的《》里提到过,那些学者级大师级的敦煌壁画临摹也不能当作原画的百分百复制品。道理也很简单,有人参与的活动,即便万分克制、即便不是出于主观动机,也难免带入个人色彩,更何况另有画风和美观度要求的插画呢?
(莫高窟第159窟原作[左]与张大千临摹,图/动脉影)
(莫高窟第98窟原图[左]与范文藻临摹)
(莫高窟第98窟常沙娜临摹[左]与潘絜茲临摹)
仅以《中国妆束》这本书来说,整体性的“二创”说明算是有的,在开头的“内容介绍”里——
本书尝试以考古发掘所见唐代文物为基础,对照传世史料或出土文书中的记载,以唐人的眼光重新解读当时真实的女性妆束时尚。
这段内容很像我们之前《》里提到的《中国传统色 故宫里的色彩美学》这本书,带着一点中文博大精深的意味在。正文里单个形象的说明也是类似的情况,既会明确标出这是哪位具体历史人物或墓主的身份,但也会说明是“参考同墓出土女俑形象绘制”“据出土服饰实物组合而成”,读者的水平也决定了他们的分辨能力。
(讨论帖评论区截图,图/小红书)
看到这个瓜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到《中国传统色 故宫里的色彩美学》的作者能不能跳出来说春晚吉祥物说明文案“照搬”他的书?因为文案中的颜色词“吐绶蓝”“龙膏烛”也符合“基于文物和历史记载的二次设计,不是文物本身”,春晚当然也是一种商用。
这里还有一个困境。我当时在《》里说《中国传统色 故宫里的色彩美学》这本书更像是文创书,做的是“文化+创意”的事情。虽然会得罪很多人,但绘本类的古代服饰、传统服饰书籍情况也十分类似。并不是说这么做是不好的,而是产品定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受众群体的定位。所谓曲高寡合,现在又叫干货没流量,文创书的受众层面必然是大于许多以往该类目下的书籍,不论是群体概率还群体定位,都会导致有许多读者既看没有分辨内容的能力,也没有分辨内容的勇气。前者关乎知识的入门与积累,后者关乎治学探究的精神。
就像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刷到一个自称做殷商服饰体验的汉服店,评论区非常质疑她的服饰考证来源,她便贴了《中华遗产》的封面与博物馆内的塑像作为依据。
(小红书相关笔记截图)
(左:《中华遗产》封面;右:安阳殷墟博物馆内妇好像)
其实这两个形象的源头都是之前发布的“数智人妇好”,且不说这类“数智人”的侧重点并不完全是形象上的考证复原(大家可以想想马王堆辛追数智人),只说看图做造型也是错得离谱,连服饰结构也完全不一样。
(左:数智人妇好全身示意图;右:某汉服店的出片)
很显然,这家汉服店没看过“数智人妇好”的相关资料(这个形象做成过衣服,上过今年的《中国国宝大会》),她看的仅有《中华遗产》封面和博物馆内塑像的半身照,尽管她也将这两者当作权威参考在评论搬出来了。这里又构成了好几对关系,这个汉服店家是上述半身像的受众,而她把店铺开在了博物馆边上,那些会转换她的顾客的参观者是这家汉服店的受众。这些受众的知识积累、学习能力和质疑精神都令人担忧。
但就像我们当年一开始也非常相信那套图一样,有些曲折算是入门的一种必然经历吧,但会有人往前走,也会有人一直原地踏步。人可以在“小白”阶段犯错,但不能一直停在“小白”阶段里理直气壮。
PS:《国色芳华》一点没看,但搜剧照的时候发现张雅钦是真好看!
感谢阅读,喜欢请记得分享哦^_^
睿迎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